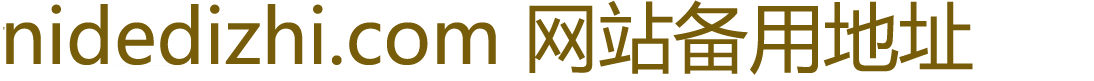
分卷阅读44
“那件事对你现在的生活有影响吗?它会让你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吗?”
“不会。”
“哎哟,那不就得了。”苏父似乎是倒了一小瓶酒,美滋滋地啜了一口,“那还有什么好记恨的,人生苦短,及时行乐都来不及,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恨别人?”他顿了一下,又补充道,“你也不用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,以后你会慢慢明白,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太容易。你爸妈我们受过的委屈比你想得要多,你那点根本不算事儿。”
苏雨眠深吸一口气,缓缓道:“我知道了。”
临挂电话前,她的目光从黑压压的高楼挪向天空,小声说:“爸,谢谢你。”
那边刚好掐了电话,也不知道听没听见。
苏雨眠刚要放下手机,就看到屏幕上跳出书法纪录片项目组的群消息。导演说他们后天准备出发去外地拍文房四宝的渊源,为期三天,包食宿,可是现在有个场务女孩生病,去不了了,需要来有人顶替她一下,让大家帮忙找找人。
苏雨眠灵机一动,在群里回复道:我我我!我可以去!我是自己人呀,又有跟组经验,还可以准备文案!
管导大手一挥:那行,就苏雨眠了。把你身份证信息发过来,给你订票。
在群里把出差的各项事宜落实之后,苏雨眠才反应过来,易聊也在这个群里。
易聊后来给她发的信息还是未读状态,头像上的小黑猫好像有点委屈。
她耸了耸肩,把手机扔到一旁,开始收拾行李。
***
关于笔墨纸砚渊源部分的拍摄,地点选在水墨之乡Z市。
这是苏雨眠第一次来Z市,天气晴好,比B市暖和一些,还没有那么拥挤繁忙,非常适合拍摄创作。
摄制团队一大早就扛着相机到了一条小胡同里,寻找隐居在这里的毛笔手艺人。
手艺人的店铺很小,家具陈设破旧,看着十分寒碜,他们要采访的那位张师傅就住在这里。
张师傅大概六旬年纪,穿着一件老旧的马甲,戴着老花眼镜,在工作台上认真地扎笔。
到午饭时间,张师傅颤颤巍巍地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冷馒头,小口小口地啃起来。
苏雨眠惊讶地问:“您就吃这个?”
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吃这个就能饱。”
摄制组有个同事拿过一份热盒饭:“张师傅,您吃这个吧。”
老人惶恐不已:“不用不用......”
“没关系,我们买多了一份,不能浪费,趁热吃吧,不然我们还得倒掉。”
老人这才放下馒头,接过盒饭吃起来。感应到苏雨眠的目光,他抬起头来,羞赧地说:“做毛笔不挣钱的,我平时主要就吃馒头。”
苏雨眠说:“您这儿的笔也卖得太便宜了,提提价不好吗?”
“那可不行,那样会把想写字的人挡在门外。”张师傅和蔼地笑笑,“书法这件事情,我得要帮忙推动才行,怎么能阻碍发展呢?”
同事插嘴道:“您别说书法了,就您这门手艺都快失传了吧?”
张师傅叹了一口气,眼神黯淡下去。
苏雨眠小声地追问同事:“怎么回事?”
同事说:“毛笔很难从外观上看出好坏,只能用良心去制作,但又挣不上钱,年轻人都不爱学。他们家制笔的工艺已经传承三代了,现在却后继无人,唉......”
张师傅也对苏雨眠说:“小姑娘,你看看我隔壁那家,原先也是个制笔店,那老头去世以后,店子盘出去,现在变成了个饮料店,什么咖什么啡的,你们年轻人爱喝的。”张师傅温和平静,“等哪天我去世了,这个店子也要关门咯。”
苏雨眠心里有些唏嘘,有种无力感油然而生,饭都有些吃不下去了。
管导瞅了她一眼,把她叫到店铺外,说:“小苏,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”他点上一根烟,眯起眼,“你所想的,就是我们拍这个纪录片的意义。”
苏雨眠默不作声。
“其实在你看不见的地方,我们国家有很多古老的手艺都在慢慢失传,制笔工艺已经算传承得不错的了。你要是往偏远一点的地方去走走,多的是连饭都吃不上的手艺人。”管导似乎已经见惯了这样的事情,语气十分平静,“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,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。所谓‘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’,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可能连独善其身都做不好,这就是现实。”
苏雨眠回过头,望着背影佝偻的张师傅,声音有些干涩,道: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?”
“你呀,好好写写旁白,争取能写点儿振聋发聩的句子。但也不要太过,毕竟是一门传统艺术,不适合奔放的风格。你自己品品吧,我觉得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
管导说得没错。
苏雨眠承认,在刚接这个项目的时候,她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一方面是觉得纪录片旁白文案没那么难写,比起原创个四五十集的电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