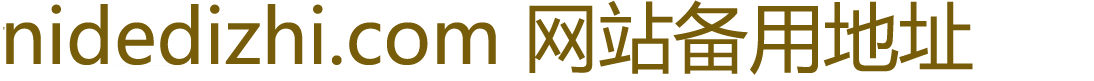
第五七七章 拖后tui的官僚ti系
然不同迁移,他们就是不给便宜祖坟。
官府这里也很着急,毕竟上级给的时间是一个月之内就要开始对移民进行分流。
于是县里将做蒲氏工作的事情压给了镇上。
镇上的主官连蒲家村都进不了。蒲鼎山让人守着村口,不让任何人进,对外声称要保卫蒲氏祖坟,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害者,博取周边百姓的同情。
他这是看准了官府不敢将他怎么样?
镇上无奈只能启动强制迁移的程序。
最后终究闹成了械斗,村民和镇上组织的民兵都有损伤。甚至连县里的守备营最后都出动了。
这件事情往重了说可以算是一场民变。最后闹出的动静不小。
要是在以往,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。满清治下,各地的叛乱多如牛毛。
但是现在已经是复兴三年了,早已经是九州安定的局面。
哪怕是一场小的民变都足以上到报纸的头条。
董书恒通过这件事情也意识到了地方宗族势力的顽固。
蒲氏完全将上面委派的村长给架空。村中的民兵也被蒲氏掌控。
当然了,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蒲氏的问题,地方官府见到谈不成就动用强制手段也不对。
办事的方式简单粗暴。
他们要是耐下心来也不是找不到突破口。
蒲氏有几个子弟在外地任职,这就是突破口,完全可以找这几个人去谈。
或者先是做好分化瓦解,从那些贫穷的族人做起工作。
村中的大多数人还是那些无地的农民。在宗族的道德绑架和对土地的渴望之间,他们是左右摇摆的。
这个时候只要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,揭穿蒲鼎山用来道德绑架那套说辞的真实面目,还是能够将这些人给争取过来的。
没有了普通族人的支持,蒲鼎山就失去了爪牙,成不了气候。
这件事情给董书恒敲响了警钟,那就是复兴军对地方宗族的削弱并不彻底。
现在随着地方上的稳定,这些宗族势力有重新崛起的势头。
另外,目前复兴军建立的官僚体系以旧文人为主。
这些人的骨子里面还是权力本位。
他们的认识深处还是那种代天牧民的一套。
所以他们在工作中会对权力过于依赖,甚至是滥用权力。
董书恒担心,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越加的严重。
这样一个思想和制度脱节的官僚体系,很可能会将他开创的大好局面给葬送掉。
董书恒不是没有想过在地方上推行评议会制度,用以监督地方官府,同时作为连接官府和百姓之间的桥梁。
但是,他又担心评议会成为地方宗族势力间接掌控的地方官府的手段。
现在复兴军的异地任职以及官员的垂直委任制度,能够将地方上的事权给集中到官府的手中,以此来压制住地方宗族势力。
满清时期,地方宗族通过县衙的胥吏掌控地方的权力,使得宗族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虽然是没有汉唐时的门阀强悍,但是这些宗族势力覆盖面广,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基础。
他们最大的危害就是掌控了社会资源,造成了社会的固化,让贫苦的农家子弟没有了出头之日。
一个社会最怕的就是阶层固化。这就像是一个人的血管被阻塞了一样,如果不及时的疏通,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疾病。
不能用地方的宗族势力,那么用什么让官府和地方建立沟通呢?
这个问题让董书恒很困扰。
他带着这个问题去问魏源。
魏源反问道:“你光是担心宗族势力,只是你有没有想过普通的百姓为什么不直接跟官府沟通呢?”
董书恒这才发现自己是钻牛角尖了。
长期以来,老百姓不愿意主动跟官府打交道。
是因为历朝历代,官府都是高高在上的。
他们是皇帝派下来管理百姓的。从来有哪个官府说自己是来为百姓服务的。
对于官府做的事情,普通百姓大都是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。
除非涉及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,而且是对他们影响极大的那种,他们才会站出来。
他们依赖地方士绅,地方士绅也一直都是以百姓的代言人自居。
仿佛,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百姓的心声。普通百姓也习惯了这样的状况。因为他们都是依附于这些士绅生活。
百姓们并不是没有情绪,只是他们更多的时候的选择隐忍。
这是一群非常善于隐忍的族群。
不过他们爆发的也非常厉害。从来没有那个民族历史上爆发过那么多的农民起义。
而且还是规模巨大的那种。
“书恒,不要着急,等到用我们的教科书教育的这一代人起来了,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成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员,不过他们却不需要